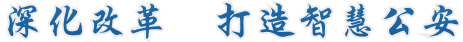【法治之窗】网暴行为不可取,如何治理有说法!
“微博站方对涉冬奥会相关内容进行排查与治理,清理违规微博41473条,对850个账号视程度采取禁言30天至永久禁言的处置”,“抖音平台通过模型识别、举报受理、舆情监测等方式,拦截清理相关违规视频、评论内容6780条,对331个存在互撕谩骂、煽动对立、网暴诋毁行为的账号,视违规情节严重程度,予以禁言甚至封禁账号等处置”......北京冬奥会赛事期间,互联网上一些不文明行为严重影响观赛氛围,多家平台重拳出击,封禁了一批极端账号,严厉打击了网络暴力、网络造谣等行为。
而前段时间的热播剧《开端》等,也让人们对网络暴力产生反思。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有了在公共空间内表达的途径,也让很多人一下子失去了应有规范。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上那些看似“不那么重要”的言行,经过互联网放大传播,很可能让网民的“声浪”变成伤人利刃。哪些行为属于网络暴力?谁是网络暴力的最大受害者?如何避免将“网络正义”变成“网络暴力”?以上种种,都成了当下需要深思的问题。
何为网络暴力?明晰定义很有必要“不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轻易作出评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谈及网络暴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林品回想起两年前的亲身经历。当时,因为发表了对某位明星的言论,在一段时间内遭受了一批极端粉丝的网络暴力。
何为网络暴力?“目前尚无明确界定,更多的是从局部角度进行归纳。比如,仇恨言论、虚假消息、暴恐言论等。”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对网络暴力作出明晰定义有其必要性,但这个定义必然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变动扩张的概念。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看来,网络暴力并不是法律用语,不同学科都可能涉及,可以看作是发生在网络公共空间里的针对特定个人的侵权行为。“这种行为往往由一个人发起、参与人数众多、公众互动频次高、具备跨平台传播等特点,其危害后果不可预测、不可控制,通常伴有侵犯人的名誉、披露人的隐私、侮辱人的尊严等侵权行为。”刘德良说。
对于网络暴力产生的原因,刘德良认为,网络具有虚拟性和匿名性,使得用户在用网过程中忽略了真实的社会身份、道德准则和规章制度,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去引导事件走向;此外,法律层面没有要求公共信息发布平台对用户信息发布行为承担事先审查义务,而只能通过事后救济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处置,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很多情况下,网络暴力蔓延背后存在网络黑产或幕后推手的恶意引导,这也导致了治理的复杂性、紧迫性。“以娱乐圈为例,很多场景下粉丝表达极易失控,网络暴力也就随之而来了。”多年关注粉丝文化的林品也深有感触。他认为,部分流量团队长期施行旨在将“粉丝型用户”规训为“数据劳工”的粉丝运营,建立了一套从“虐粉—固粉”到“撕资源—争番位”再到“催氪金—割韭菜”的链条,其背后的商业、资本因素需要警惕、批判。
从法律视角透视网络暴力网络世界是与真实世界并行、交融的世界。因此,网络空间从来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在网上的言行超过言论自由的合理边界,都将承担相应后果、付出法律代价。从近年来的网络暴力事件司法判决看,较有影响的两起案件分别是“德阳女医生安某遭网络暴力后自杀案”和“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诽谤案”。
其中,杭州女子被造谣案件中分别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德阳女医生案件中法院认定三名被告人行为均已构成侮辱罪,依法判处被告人常某一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常某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孙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案件不胜枚举。对此,刘德良阐述了自己的担忧:“传统的法律法规采取事后救济的方式,并不能完全适应网络领域的变化。互联网时代信息后续传播成本低,控制后续传播较为困难,事后救济的方式已不符合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因此,互联网立法必须及时跟进,并加大执法力度,切实制止网络暴力现象,净化网络环境。”
深入剖析这些案例可以发现,网络暴力蔓延中时常伴随着人肉搜索等乱象,这也凸显了个人信息、个人隐私的泄露问题。“个人信息、数据的泄露是造成网络暴力事件影响力扩大的重要环节。因此,在网络暴力治理过程中,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水平和数据安全水平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吴沈括说。
在去年11月份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提到了要加强重要互联网平台的义务,以及强化侵犯个人信息的惩罚机制和力度。对此,刘德良认为,网络侵权具有匿名性特征,被侵权人无法知晓实施侵权行为的直接主体,因此网络服务商作为信息发布平台的提供者,理应在其能力范围内,向被侵权人披露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信息,以便被侵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哪些网民更易成为施暴者和受害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在2019年时曾针对上海部分地区的中学生做过问卷调查,其中认为遭受或见证过网络暴力的学生占比将近90%。“我们特别担心的是,在‘如果遭受到了网络中的语言暴力或人身威胁,你会选择怎么办’这个问题下面,排名最高的是选择自我消化,排名最低的则是告诉老师或家长。这说明家长和学校没有跟孩子建立足够的信任,也没有让孩子意识到遭遇网暴也可以求助。”董晨宇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6至19岁网民规模达1.58亿,占网民整体的15.7%。随着触网年龄结构进一步向青少年群体扩大,互联网对青少年群体的不良影响也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董晨宇表示,在前互联网时代,人们更关注现实中的校园暴力,这时候家长会有意识地告诉孩子,“如果有人欺负你,就告诉家长或老师”;但在互联网时代,学生很可能不会主动说,“老师,有人在网上骂我”。
“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对这种转变进行足够有效的干预,这本身也是媒介素养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董晨宇认为,从“网络去抑制效应”的影响来看,网络会抑制一些广义上的“社会规范”,很多时候网上互动无法得到及时反馈,网络暴力发生时施暴者看不见受暴者,施暴者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施加伤害,让很多本可讨论的问题变成了一场“网上骂战”,导致理性、温和、建设性的言论被挤压或屏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参与网络暴力的网民多是年龄较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用户。他们对自己的观点信心非常足,但实际上知识非常有限。”林品说,他们需要通过攻击别人来满足“自己是正确的”想象。此外,很多娱乐圈粉丝时常会陷入流量明星团队的粉丝运营人员、“职业粉丝”、“粉头”为其搭建的信息茧房内,并在“茧房”内频繁接收各种低质量、非理性的信息,导致精神和情感受到持续性刺激,容易陷入非友即敌、非粉即黑的二元对立思维,对网络空间中丰富多元的声音进行非此即彼的划分。
此外,从人格特质方面来看,董晨宇认为,施暴者往往具有侵略性人格,并极其缺乏同理心。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侵略性人格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将模棱两可的信息解读为敌对信息。
网络文明需要多方发力、久久为功“网络暴力治理需要重视多方面因素:既要通过引导教育的方式,提升公民的媒介素养、文明素质,也要通过完善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机制,促进互联网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林品说。
“要采取事先预防与事后救济相结合的方式遏制网络暴力。”刘德良建议,网络信息传播离不开网络平台,要先从规制平台入手,在法律中明确平台的事先审查责任,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图片、文字、语音等进行识别,过滤显而易见的违法侵权信息,对于其他较为隐蔽的侵权信息,可由受害人通知平台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限制公民肆无忌惮地在网上发表言论,这样也可以在网络暴力发生后及时追究责任;加大对侵权人或不履行主体责任平台的法律责任追究,降低维权人成本,提高侵权人成本,既是对受害人的救济,也是对侵权人的震慑与遏制。
在监管机制完善方面,吴沈括认为,要及时建立有效地投诉举报机制,保证能够快速、有效、便捷地处理民众的投诉和举报,“这样可以让网络暴力及早被发现,扼杀在萌芽状态下”。
为了营造文明健康、喜庆祥和的春节网上舆论氛围,今年春节前夕,中央网信办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清朗·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包括集中整治网络暴力、散播谣言等问题。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各地网信部门、互联网平台积极响应,集中开展网络暴力专项整治。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通过互联网纽带作用形成的虚拟空间,加强文明社会建设也要加强网络文明、网络伦理建设。“很多线上问题是线下问题在网络上的映射,并在网络空间表现出特殊的形式和传播规律。因此,只有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治理网络暴力。”吴沈括说。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王四新也表示,治理网络暴力要从网络空间言论、信息生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矫正,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
- -- 北京市公安局 --
- -- 天津市公安局 --
- -- 上海市公安局 --
- -- 重庆市公安局 --
- -- 河北省公安厅 --
- -- 山西省公安厅 --
- -- 内蒙古公安厅 --
- -- 辽宁省公安厅 --
- -- 吉林省公安厅 --
- -- 江苏省公安厅 --
- -- 浙江省公安厅 --
- -- 安徽省公安厅 --
- -- 福建省公安厅 --
- -- 江西省公安厅 --
- -- 河南省公安厅 --
- -- 湖北省公安厅 --
- -- 湖南省公安厅 --
- -- 广东省公安厅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
- -- 海南省公安厅 --
- -- 四川省公安厅 --
- -- 贵州省公安厅 --
- -- 云南省公安厅 --
- -- 甘肃省公安厅 --
- --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 --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 --
- -- 西藏自治区公安厅 --